日期:2021-05-11 15:05:16 来源: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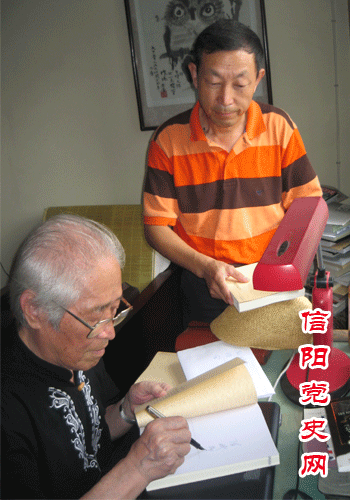
图为白桦先生(左)在其新近出版的散文集《不再重现的图画》一书上为本文作者题写赠言
(摄影:《光明日报》社记者 孙明泉)
中秋佳节,我们从河南信阳出发一路兴匆匆地赶到上海,拜访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白桦先生。《光明日报》社记者孙明泉与白桦先生事先有约,先行抵达。白桦先生因在西安未及赶回,虽然见面的时间推延到次日,却应了一句俗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一个很好的兆头。现代都市,茫茫人海,上海之大,先生何在?摊开上海市区地图,一眼看到静安区,“静则安”,先生追求文学追求真理,一生坎坷,虽九死犹未悔,先生暮年当寓此处!仅凭直觉,我们就打的直奔里,找一家旅馆住下,接通电话,果然先生的住处与我们近在咫尺。
白桦先生是我们信阳市平桥区人,敬仰之外,我们自然而然还别有一番老乡的亲切滋味,但是他毕竟又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况且已年近八十高龄,选择中秋节这种时候来打扰他老人家是不是合适呢?怀着一丝疑虑和担心,我们来到他家门口,发现先生和夫人王蓓女士已经早早等候在门口了。没等我们多作介绍,白桦先生就说,老伴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看演出跌了一跤,刚才还躺着养伤呢!听说咱们家乡来人,赶快穿衣起来迎接,伤痛也好了。一句话让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房间顿时溢满了乡情乡音。这是一间客厅兼书房的普普通通的房间,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先生心鹜八极神游万仞,而却置身于这斗室之间。此情此景此时,我们对先生更加敬佩的同时,先前的些许拘束早已烟消云散。
我们问先生还能说家乡话吗?白桦先生先是爽朗地一笑,接着不无遗憾地说,实在是说不好了,真是久违故乡了。我们原以为白桦先生的故居在五里镇,见面后经他介绍才知道其实是在平桥镇的钟山铺,与我的老家越说越近了。我的父亲和白桦先生是同龄人,生在与其田搭界地相连的邻村,祖父母早亡,少年时代开始父亲就到钟山铺流浪谋生。他曾经多次给我讲过钟山铺有个陈汉章,宁死不伺候日本人,惨遭日本宪兵活埋的故事。原来故乡这位大名鼎鼎的陈汉章,就是白桦先生的父翁。说话之间,平桥区委书记张明春的电话打了过来,问我们“见到了没有?一定代我向老人家问个好!”我们顾不上回话,随手把手机递给了眼前的白桦先生。提起故乡,先生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可惜当时由于我过分相信录音机这种所谓现代化的玩意儿,而没有认真做笔记,结果录音机出了毛病,并没有为我们记下先生弥足珍贵的教诲。回想起来,他的谈话让我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白桦先生曾经屡次强调,我们的家乡原信阳县自古以来就是“闻县名邦”。
在我们围绕一个“乡”字,三皇五帝海阔天空而不知日之中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听得最认真而又极少插言,这个人就是当年的金陵佳媛如今的白桦夫人王蓓女士。除了饶有兴致听我们用乡音“侃大山”之外,她老人家还一遍一遍地关照我们喝饮料,并且反复解释如果不是快吃午饭了她一定为我们“上茶”,看到我们的饮料没喝,她又亲自为我们一一拧开密封的饮料瓶盖。也许一般人不会想像得到,这位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宛如寻常家庭主妇似的老妈妈,却是在共和国的电影星空创造过辉煌,曾经出演过《武训传》、《乌鸦与麻雀》、《大浪淘沙》等十八部巨片的影星。
这次拜访,我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目前我们正在编纂《平桥经典》,一部旨在介绍平桥历史和现状,向国内外全面推介平桥的书籍。白桦先生是我们故乡的骄傲,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影响,文中辟有专节介绍。我们深知以我们学识之浅陋笔力之微弱,纵有千丈热忱万般深情,也难得写出先生绩业、风神、德望之万一。此行目的,就是将我们介绍白桦先生的一节文字送给他亲自把关。我们说明来意之后,白桦先生当即就答应下来。看他如此爽快,我们又得寸进尺请他为《平桥经典》作序,先生表示非常理解,温和地笑着说,让我看完书稿再写吧。
在浓浓的乡情乡音里,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超过十二点半。我们表示要找一个像样的饭店宴请先生,代表书记、区长表达家乡人的一片心意。白桦先生说,家乡父母官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不必破费,那些豪华的地方,往往有名无实。说完起身领我们到马路对面就近找了一家普通饭店。看着两位老人和我们一起步行,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我们本来是打算到《光明日报》社上海记者站借车,不巧车辆外出未能如愿。我们向先生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歉意,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点路程算得了什么,我经常爬山,昨晚朋友为我接风我们喝酒还喝到十二点呢!说这话时我们这才注意到,先生果然一直走在我们前面。他那亦古亦雅的黑色绣花对襟上褂、黑白亮泽而略显飘逸的头发,让我们相信先生依然还是年轻时代那个青春浪漫执著的先生,谈笑之间似乎能够感受到他那澎湃的激情、燃烧着的一颗不泯的诗心。
宴席上,先生不时为我们介绍一些鲜有所闻的家乡掌故,介绍他青少年时代家乡的风情、世相、习俗、趣闻以及山脉河流、美味佳肴,当然也离不了回忆他在信阳师范学习期间从事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情不自禁之中,我随口朗诵了一段白桦先生五十年代的诗作:
含泪的云飘去了,
月亮就是大地的银灯;
听我唱一支歌吧,年轻的朋友!
叮咚的流水就是我的琴……
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们同学之间口耳相传令我记忆犹新的一段优美诗句,其实一直到见到白桦先生为止,时隔30多年我还一直没有找到“文字根据”,此时有心想在白桦先生这里当面“证实”一下。白老听了以后很高兴地笑了笑说,“你记得很准确,《孔雀》长诗开篇就是这一段。”当我们提及先生青年时代就从挚爱文学到追求真理、投笔从戎时,先生回答那是因为他们“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先生说得轻描淡写,但是从他那略显深思的眉宇之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生的思绪一定回到了那个他所亲历过的波澜壮阔的年代,那个烙印下他艰难坎坷足迹的人生旅途。此情此景,我似乎有一个预感,先生思想的闸门已经开启,先生情感的琴弦已经拨动,我们期待着,他一定会为我们的家乡浓墨重彩挥洒一笔!
在白桦先生沉浸在对故乡的怀想之时,我们且不妨对这位家乡赤子的文学生涯作一些简单的追踪。
白桦的儿子曾在一封信里劝他说:“爸爸!你不能改变一种方式生活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你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先生的回答则是:“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够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因为我的选择似乎和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没有关系,而是对生活执着的爱。我不能用生命意义这样昂贵的代价去换取宁静和舒适的生活……四十年代中叶,我曾在出国留学和为一个新中国而在自己的土地上牺牲奋斗之间进行过选择。”
白桦出生于1930年,那是一个民族危亡的年代,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1938年深秋,八岁的他随着父母逃亡到深山里。有一天夜晚,日军的枪声渐渐远去,惊魂未定的难民们点燃了篝火,躺在火边歇息。一个识字的难民在行李中拿出一册破旧的唱本来,那人唱着唱着就声泪俱下了。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后来,他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一群孤雏在铁蹄下挣扎。不久,他就成了一个唱本的小小吟唱者。中学时期,他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5岁时便以白桦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诗作。然而1947年,为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中国,他带着自己对真理、对文学的执著追求,毅然加入到解放新中国的战斗行列。
1952年,因为文学方面的成就,作为一个22岁边防军基层军官的白桦,奉命来到贺龙元帅身边,记录贺老总的战斗经历。文艺之神缪斯似乎格外青睐这位春风得意的年轻诗人。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白桦在北京六里桥莲花池受审,被打成右派,自此以后一连串的厄运接踵而来。从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白桦的小说、诗歌和电影,在文革中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因为撰写剧本《李白与杜甫》,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
1957到1976年二十年间,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他曾发誓放弃文学,把所有的笔记、日记甚至连笔全都毁掉。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义无反顾地把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八十年代,他的创作激情迸发,进入了创作的丰收期,各种文学体裁均有尝试,硕果累累,反响强烈。他的兄长叶楠也以《甲午风云》、《傲蕾·一兰》、《巴山夜雨》等优秀影片蜚声中外。连续几年兄弟二人的电影作品竟占国产影片的三四分之一。兄弟二人同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之奠堂,成为一时风景,双双成为中国文坛、影坛巨星。
文革一过,身心解放的白桦兴奋起来,根据贺龙元帅早年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一部话剧《曙光》。描写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洪湖的故事,那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件,他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由此惹来风波。因为人们承认它的真实,但又接受不了它的真实。
1980年由他创作的影片《今夜星光灿烂》,仍然是一场真伪之争。有人批评作品宣扬了人道主义,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强硬地用剪刀删减之后才得以和观众见面,同时在报上展开公开批判。所幸已是文革之后,读者已经敢怒而且开始敢言了,这场批判也就草草收场。
1980年,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的电影《太阳和人》,因为表达了一代人对现实政治的怀疑而受到严厉批判,再次引起一场全国性的震荡。这次对影片的批判活动,成为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观念的较量。
纵观白桦一生,可用文天祥的诗句“辛苦遭逢起一经”来概括。然而,对于他自视为生命的文学,白桦却“至今都怀着一个奢望,那就是在有生之年给这个冷暖世界留下一朵不死花!”打开四卷本《白桦文集》,那凄美动人的叙事长诗:《孔雀》、《鹰群》;那清新隽永的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一首诗歌的来历》;那曾经感染和震撼过我们心灵的剧本、影视作品:《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苦恋》、《孔雀公主》以及《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那篇篇脍炙人口让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不正是白桦先生在是与非、荣与辱、爱与恨、灵与肉、雷与电的炼狱煎熬之中,用他的血泪与生命,为生养他的祖国、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留下的朵朵不朽之花吗!
告别白桦先生,第三天我们就收到他的电子邮件。我们所写关于他的一段文字他已经改好,所谓“改”,只不过是一些年月、数据、史料之类,至于我们文笔之拙、评介之谬则一字不动,足见先生大家风范,无比旷阔包容之胸怀。很快,我们又无比欣喜地收到先生为我们所写的序言———一曲洋洋六千字的乡情乡音,一份凝聚八秩老人挚情与心血的献给家乡的厚礼。
在《平桥经典》即将付梓之际,手捧书稿再一次目叩序言,我们又仿佛回到和白桦先生对面倾谈的那一刻。先生建议我们不仅要从现实认识家乡,而且要多从历史中了解故乡,并告诉我们,《左传》就对平桥(原信阳县)早有记载。以我们浅薄的历史常识所知,春秋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当年首封于申地(信阳)——故而信阳自古以来就以“申”相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办报纸还有《申城晚报》。而后,春申君又曾经加封上海一带,上海始得“申城”之名。若以时序记之,“申城”之名信阳当在上海之先;若以渊源而论,则上海、信阳皆为申国故土、“闻县名邦”,血脉所系,一脉相承。白桦先生生于信阳奔波四方而定居上海,游子千里,叶落归根,信阳、上海亦无外乎此申城彼申城而已。天意乎!宿命乎!
(本文作者系信阳市平桥区委办副主任、党史研究室主任)